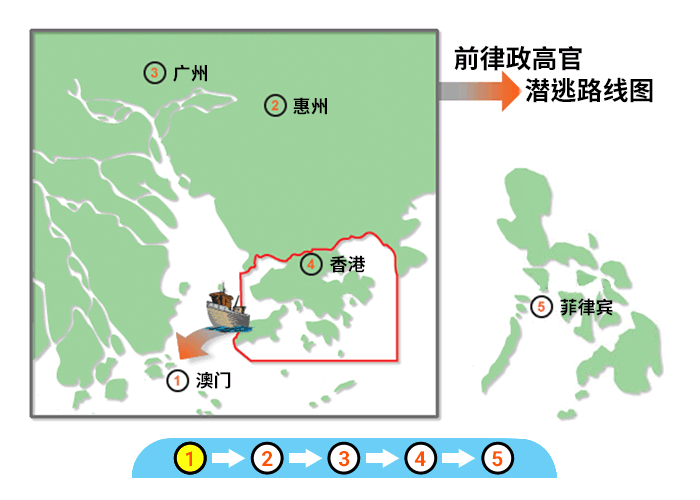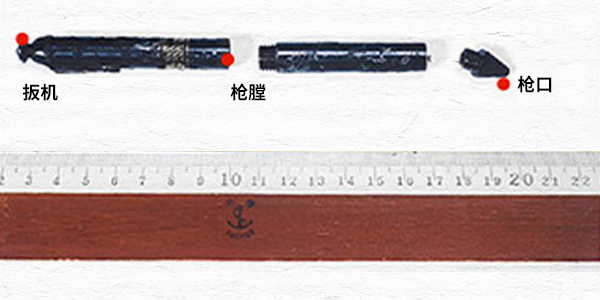财富 来历不明
「最初我们拘捕该名前律政官员时,有些人以为是我们弄错了,而相信他是无辜的。当时,他的事业如日方中,稳坐前律政署第三把交椅,人们认为他根本不可能亦没需要贪污。」廉署专案小组成员总调查主任包理正(见右图)忆述。
包理正指出廉署是于89年8月接获一位化名为「苹果」的线人提供的情报,继而展开了这个代号为「耶路撒冷」的调查行动。调查不久,廉署已发现这名年薪约为五十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单在86至87年间,财富增长逾百万港元之多。
由于这名前律政官员,正处理数宗商业大案,为免该名官员所负责的案件受其影响,不能得到公平审讯,廉署人员掌握了初步证据后,在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卢彬亲自率领下,于89年10月27日到这名官员香港的寓所把他拘捕,同时也拘捕了两名涉嫌贿赂该名官员的私人执业律师,准予他们各人自签五万港元保释,但须交出旅游证件。
廉署并即时向律政司申请勒令该名官员停职受查,并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14条要求他于28天内解释其财富来源。该名官员虽要求延长解释期至56天。但其后在未有提交合理解释前而弃保潜逃,案件亦正式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