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审讯
控罪
在2017年10月16日,第一被告(路政署总工程监督)及第二被告(分判商),被落案起诉下列罪名,其后于观塘裁判法院提堂。
第一被告,被控违反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贿赂条例》第4(2)(a)条:
身为公职人员,于或约于2015年9月8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而从第二被告接受利益,即接受形式为金钱的五万元馈赠、贷款、费用、报酬或佣金,作为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经作出或不作出凭其公职人员身分而作的行为(即倾向于或保持倾向于优待承建商S、A工程公司、B工程公司、C工程公司及/ 或D工程公司)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他作出或曾经作出上述行为而接受该利益。
第二被告,被控违反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
于或约于2015年9月8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无合理权限或合理辩解而向公职人员,即第一被告,提供利益,即提供形式为金钱的五万元馈赠、贷款、费用、报酬或佣金,作为该第一被告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经作出或不作出凭其公职人员身分而作的行为(即倾向于或保持倾向于优待承建商S、A工程公司、B工程公司、C工程公司及/ 或D工程公司) 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他作出或曾经作出上述行为而向他提供该利益。
重要的DNA证据
由于本案件只得环境证据,所以能否成功起诉,DNA证据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
政府化验所的化验报告指出,在第一被身上检取的信封及纸币的表面,均找到以第二被告为主要来源的DNA混合物。
控方认为这五万元是第二被告给第一被告的,但辩方却认为有关DNA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点,因为第二被告的DNA有可能透过间接途径沾在这些纸币上。
专家证人(政府化验师)公正地表示,她不能够绝对排除信封及纸币上带有的第二被告DNA,并不是直接来自第二被告的可能性,例如是经握手传送等。她进一步解释说:「然而在这情况下,最后接触物件者留下的DNA,应该比间接接触者留下的DNA多;后者留下的DNA的数量不会多至成为主要来源。」
虽然专家证人不能够绝对地排除「间接接触」而留下DNA的可能性,但辩方没有证据支持间接接触这说法。再者,第二被告的DNA混合物不单在一种物件上被发现,而是分别留在多处不同的地方。
法官没有忽略第二被告的DNA可经间接接触而留下的可能性,但由于完全没有证据显示第二被告的DNA会经过哪一种间接接触方式传送到第一被告身上的物件,第二被告经间接接触而留下DNA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案中的证据,裁判官认为唯一及不能抗拒的推论是,以信封装载的纸币,是第二被告交给第一被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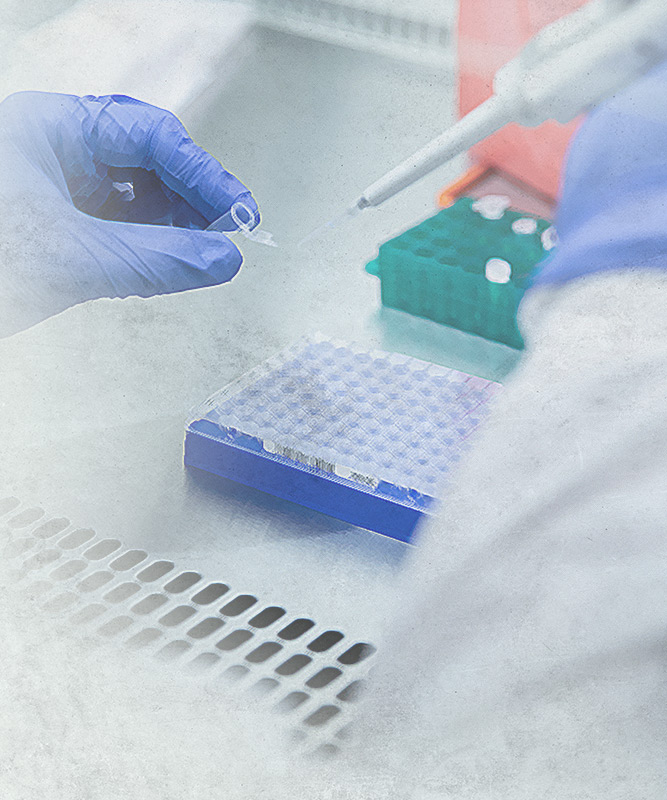
贿款vs.「甜头」
控辩双方另一个争拗点,是那五万元到底是针对任何特定的行为的诱因或报酬(quid pro quo),还是纯粹是为了保持良好关系的「甜头」(general sweetener)?
根据判词,法官认为控方检控基础十分清晰——该五万元并非作为与隧道工程有关的指定作为的诱因或报酬,而是作为第一被告凭其公职人员身份,「倾向于或保持倾向于优待」第二被告及与其有关的公司的诱因或报酬,即是一般所称的「甜头」。
第一被告身为公职人员,有权批准及建议观塘区道路维修工程,这些工程由承办商S进行。而第二被告曾是承办商S于观塘区道路工程的地盘总管,承办商S亦有把工程下判给第二被告持有股份及担任董事的工程公司——两名被告工作上有密切的关系,第二被告亦可因第一被告批准或建议的工程而获益。二人必然知道他们之间有利益冲突,应尽量避免往来。
为何第二被告要给第一被告这笔数目不少的现金,而且更在第一被告开始隧道工程拨款申请不久后及即将调职前交给他?在这些环境证据之下,法官绝对有权作出无可抗拒的推论——该五万元是作为第一被告「倾向于或保持倾向于优待」与第二被告有关的公司的诱因或报酬,而两名被告在接受及提供该笔利益时有贿赂意图。
没有证据显示两名被告有工作以外的关系,控方亦一再强调二人的公务关系,纯粹是提出第一被告接受「甜头」的背景事实证据,用以证明该五万元是与职务相关,但却与第一被告提出隧道工程拨款申请的特定行为无关。法官认为,「唯一及不能抗拒的推论是」,该五万元与第一被告的职权有「一般的关连」。因此裁定两名被告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