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審訊
控罪
在2017年10月16日,第一被告(路政署總工程監督)及第二被告(分判商),被落案起訴下列罪名,其後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第一被告,被控違反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4(2)(a)條:
身為公職人員,於或約於2015年9月8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從第二被告接受利益,即接受形式為金錢的五萬元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作為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行為(即傾向於或保持傾向於優待承建商S、A工程公司、B工程公司、C工程公司及/ 或D工程公司)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或曾經作出上述行為而接受該利益。
第二被告,被控違反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第4(1)(a)條:
於或約於2015年9月8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理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公職人員,即第一被告,提供利益,即提供形式為金錢的五萬元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作為該第一被告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行為(即傾向於或保持傾向於優待承建商S、A工程公司、B工程公司、C工程公司及/ 或D工程公司) 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或曾經作出上述行為而向他提供該利益。
重要的DNA證據
由於本案件只得環境證據,所以能否成功起訴,DNA證據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
政府化驗所的化驗報告指出,在第一被身上檢取的信封及紙幣的表面,均找到以第二被告為主要來源的DNA混合物。
控方認為這五萬元是第二被告給第一被告的,但辯方卻認為有關DNA證據,不足以證明這點,因為第二被告的DNA有可能透過間接途徑沾在這些紙幣上。
專家證人(政府化驗師)公正地表示,她不能夠絕對排除信封及紙幣上帶有的第二被告DNA,並不是直接來自第二被告的可能性,例如是經握手傳送等。她進一步解釋說:「然而在這情況下,最後接觸物件者留下的DNA,應該比間接接觸者留下的DNA多;後者留下的DNA的數量不會多至成為主要來源。」
雖然專家證人不能夠絕對地排除「間接接觸」而留下DNA的可能性,但辯方沒有證據支持間接接觸這說法。再者,第二被告的DNA混合物不單在一種物件上被發現,而是分別留在多處不同的地方。
法官沒有忽略第二被告的DNA可經間接接觸而留下的可能性,但由於完全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的DNA會經過哪一種間接接觸方式傳送到第一被告身上的物件,第二被告經間接接觸而留下DNA幾乎是不可能的。根據案中的證據,裁判官認為唯一及不能抗拒的推論是,以信封裝載的紙幣,是第二被告交給第一被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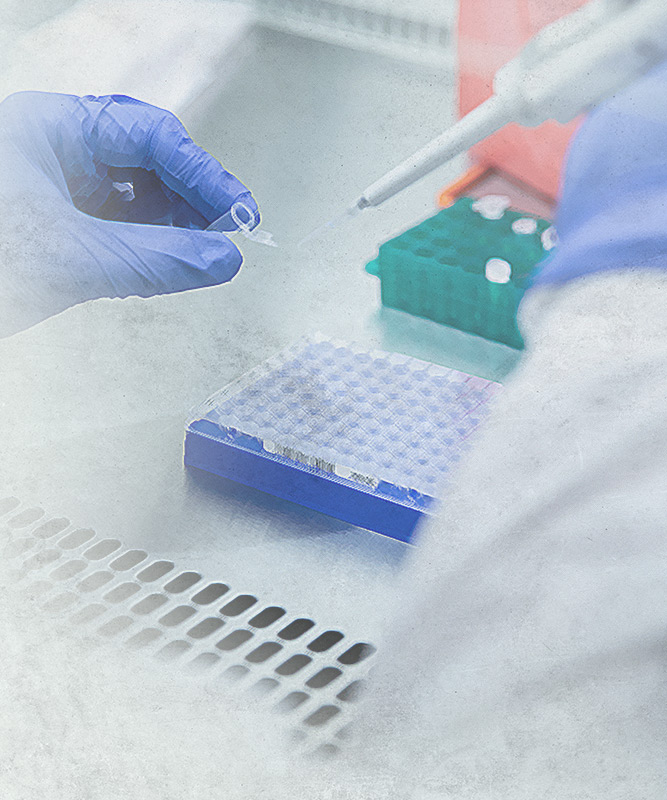
賄款vs.「甜頭」
控辯雙方另一個爭拗點,是那五萬元到底是針對任何特定的行為的誘因或報酬(quid pro quo),還是純粹是為了保持良好關係的「甜頭」(general sweetener)?
根據判詞,法官認為控方檢控基礎十分清晰——該五萬元並非作為與隧道工程有關的指定作為的誘因或報酬,而是作為第一被告憑其公職人員身份,「傾向於或保持傾向於優待」第二被告及與其有關的公司的誘因或報酬,即是一般所稱的「甜頭」。
第一被告身為公職人員,有權批准及建議觀塘區道路維修工程,這些工程由承辦商S進行。而第二被告曾是承辦商S於觀塘區道路工程的地盤總管,承辦商S亦有把工程下判給第二被告持有股份及擔任董事的工程公司——兩名被告工作上有密切的關係,第二被告亦可因第一被告批准或建議的工程而獲益。二人必然知道他們之間有利益衝突,應盡量避免往來。
為何第二被告要給第一被告這筆數目不少的現金,而且更在第一被告開始隧道工程撥款申請不久後及即將調職前交給他?在這些環境證據之下,法官絕對有權作出無可抗拒的推論——該五萬元是作為第一被告「傾向於或保持傾向於優待」與第二被告有關的公司的誘因或報酬,而兩名被告在接受及提供該筆利益時有賄賂意圖。
沒有證據顯示兩名被告有工作以外的關係,控方亦一再強調二人的公務關係,純粹是提出第一被告接受「甜頭」的背景事實證據,用以證明該五萬元是與職務相關,但卻與第一被告提出隧道工程撥款申請的特定行為無關。法官認為,「唯一及不能抗拒的推論是」,該五萬元與第一被告的職權有「一般的關連」。因此裁定兩名被告罪名成立。